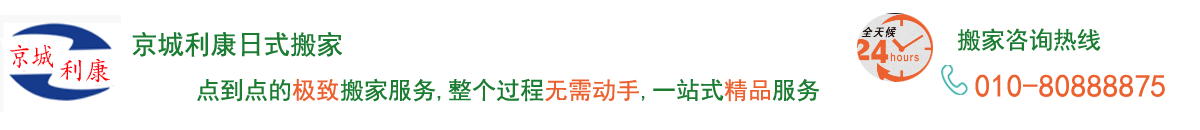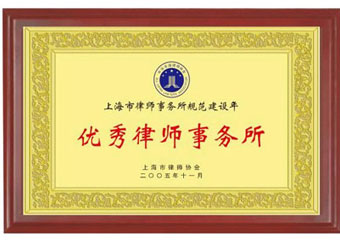1982年,R訴Caldwell一案引發(fā)了爭(zhēng)議。在Caldwell案中,被告在自我陶醉的情況下,放火燒了他曾經(jīng)工作過(guò)的酒店。他被判定犯有兩項(xiàng)指控,一項(xiàng)是縱火罪,另一項(xiàng)是根據(jù)《刑事?lián)p害法》第1(1)條。被告聲稱,他當(dāng)時(shí)喝得太多,確實(shí)沒(méi)有想到他放火的酒店里還有人。因此,這引發(fā)了客觀魯莽測(cè)試的 "誕生"。這是因?yàn)椋绻ㄔ鹤裱矊幇驳臋z驗(yàn)標(biāo)準(zhǔn),即被告必須意識(shí)到風(fēng)險(xiǎn)的存在,那么被告就會(huì)被宣告無(wú)罪,因?yàn)樗淖砭茽顟B(tài)會(huì)影響他的判斷力。法院不愿意僅僅以他沒(méi)有意識(shí)到風(fēng)險(xiǎn)為由宣布他無(wú)罪,這完全是由于他的過(guò)錯(cuò),即自我中毒。為了防止這種情況,法院試圖填補(bǔ)坎寧安測(cè)試中的漏洞。勛爵們普遍決定,如果法規(guī)使用 "魯莽 "一詞,將適用不同的測(cè)試。迪普洛克勛爵說(shuō),一個(gè)人對(duì)于財(cái)產(chǎn)是否被毀壞或損壞是魯莽的。"如果(1)他所做的行為事實(shí)上造成了財(cái)產(chǎn)被破壞或損害的明顯風(fēng)險(xiǎn),并且(2)當(dāng)他做這個(gè)行為時(shí),他(i)沒(méi)有考慮到存在任何這種風(fēng)險(xiǎn)的可能性,或者(ii)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存在一些風(fēng)險(xiǎn),但還是去做了。根據(jù)這兩個(gè)方向,必須證明所冒的風(fēng)險(xiǎn)是 "明顯 "的。意思是說(shuō),Caldwell測(cè)試要求,即使被告沒(méi)有看到風(fēng)險(xiǎn),一個(gè)合理的人也會(huì)察覺(jué)到。因此,如果被告確實(shí)考慮過(guò)此事,但確實(shí)沒(méi)有察覺(jué)到任何風(fēng)險(xiǎn),而這并非他的過(guò)錯(cuò),那么就會(huì)產(chǎn)生被告的責(zé)任問(wèn)題。因此,Diplock勛爵制定的 "示范指示 "含有不一致和漏洞,這將在隨后的幾段中討論。
現(xiàn)代刑法中最重要的過(guò)錯(cuò)要素之一是魯莽。與意圖一樣,盡管一般來(lái)說(shuō)不那么容易受到責(zé)備,但在確定犯罪意圖時(shí),它可能是一個(gè)相當(dāng)復(fù)雜的概念。在過(guò)去,對(duì)于這種確定過(guò)失的正確方法一直存在很大的爭(zhēng)論。在我們研究法律中魯莽行為的發(fā)展之前,首先讓我們研究法律設(shè)定正確的平衡意味著什么。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假設(shè)正確的平衡是指在社會(huì)背景下,在追究個(gè)人責(zé)任時(shí)確立的正義與維護(hù)法律之間的 "妥協(xié)"。關(guān)于魯莽行為的法律起源于1861年的《惡意損害法》第51條,該條規(guī)定:"任何非法和惡意造成任何損害的人......都是犯了輕罪......" Pembliton是一個(gè)根據(jù)該條款指控被告的案例。在這里,法院將 "惡意 "解釋為所做的行為必須是有意和故意的,而罔顧所感知的風(fēng)險(xiǎn)就足以作為意圖。在R v Faulkner案中也同樣采用了這種方法。

在R訴Cunningham案中,Pembliton被作為依據(jù)。在Cunningham案中,被告人偷了一個(gè)煤氣表。煤氣泄漏,危及吸入煤氣的受害者的生命。法院批準(zhǔn)了Pembliton的原則,判定被告犯有惡意施用有毒物質(zhì)以危害生命的罪行。刑事上訴法院引用了"......'惡意'必須被認(rèn)為不是......(作為)一般的邪惡,而是要求(i)有實(shí)際的意圖去做事實(shí)上所做的特定類型的傷害,或者(ii)不顧這種傷害是否會(huì)發(fā)生(即:被告已經(jīng)預(yù)見(jiàn)到特定類型的傷害可能會(huì)發(fā)生,但仍然去冒這個(gè)風(fēng)險(xiǎn))。" 因此,法定犯罪中的惡意必須假定對(duì)后果的預(yù)見(jiàn),不要求對(duì)受害者有任何惡意。坎寧安的魯莽測(cè)試是一種主觀形式的犯罪意圖,側(cè)重于被告人自己對(duì)風(fēng)險(xiǎn)的感知。該測(cè)試要求證明他承擔(dān)了不合理的風(fēng)險(xiǎn),也要求證明他在選擇承擔(dān)風(fēng)險(xiǎn)之前意識(shí)到了這種風(fēng)險(xiǎn)的存在(盡管可能是明顯的)。隨后,Mowatt也依賴于Cunningham案的先例。雖然在Cunningham案中,法院特別考慮了惡意的要求(魯莽的形式),但該測(cè)試可以普遍適用于其他類型的魯莽行為。
1969年,法律經(jīng)歷了一次改革。法律委員會(huì)審查了具體的罪行,包括惡意損害的法律。坎寧安測(cè)試被批準(zhǔn)。法律委員會(huì)認(rèn)為,做出被禁止的行為的 "意圖 "或?qū)ζ浔唤沟暮蠊聂斆?"現(xiàn)有惡意損害罪的基本精神要素"。法律委員會(huì)還表示傾向于使用 "故意 "或 "魯莽 "而不是 "惡意 "的字眼。在第31號(hào)工作文件中,委員會(hu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則,這些原則被稍作修改,并被納入后來(lái)頒布的1971年《刑事?lián)p害法》第1(1)條和第1(2)條。另一方面,《1861年惡意損害法》的大部分內(nèi)容都被廢除了。R訴Stephenson案是該法頒布后的一個(gè)重要案例,該案考慮了《刑事?lián)p害法》第1(1)條中 "魯莽 "的含義。
R訴Lawrence案與Caldwell案也是在同一天判決的。在隨后的幾年里,這兩個(gè)案件的原則被認(rèn)為適用于所有與魯莽有關(guān)的罪行,就像Elliot v C一樣,除非議會(huì)規(guī)定。2003年,R訴G和其他人重新審查了魯莽的定義,重新回到了其主觀形式。該案涉及兩名未成年人,他們點(diǎn)燃了一些報(bào)紙并將其扔到了垃圾桶下面。一場(chǎng)大火發(fā)生了,造成了價(jià)值約100萬(wàn)美元的損失。隨后,根據(jù)1971年《刑事?lián)p害法》S1(1)和(3),他們被指控犯有縱火罪,并在一審中被宣布有罪,因?yàn)橹鲗彿ü俑鶕?jù)Caldwell的規(guī)定指導(dǎo)陪審團(tuán)。然而,上議院重新考慮了關(guān)于法律問(wèn)題的決定,并采用了法律委員會(huì)的《刑法典草案》的定義。雖然這個(gè)定義是基于坎寧安案的原則,但上議院所依據(jù)的是這個(gè)定義,而不是其先前在那里的文字。坎寧安的定義和法典草案之間有3個(gè)主要區(qū)別。首先,前者只提到了作為結(jié)果的冒險(xiǎn),而不是像后者那樣作為一種情況。其次,與坎寧安的測(cè)試相比,法典草案有一個(gè)額外的限制,即被告人的冒險(xiǎn)行為必須是 "不合理的"。為了確定冒險(xiǎn)行為是否不合理,法院必須平衡風(fēng)險(xiǎn)的嚴(yán)重性和被告行為的社會(huì)價(jià)值等因素。另外,坎寧安測(cè)試只要求預(yù)見(jiàn)到實(shí)際發(fā)生的傷害,但有人認(rèn)為,法典草案要求意識(shí)到實(shí)際造成的損害可能發(fā)生的風(fēng)險(xiǎn)。
另外,為了彌補(bǔ)坎寧安的 "漏洞",迪普洛克勛爵在G案中正確地指出,法院將。"......當(dāng)被告說(shuō)他的腦海中從未出現(xiàn)過(guò)某種風(fēng)險(xiǎn)的想法時(shí),決定是否可以相信他",陪審團(tuán)不會(huì)盲目地接受被告的減刑。
由于各種原因,Caldwell被否決了,最重要的是合理的人的假設(shè)。在Smith和Hogan案中,有一個(gè)比喻來(lái)說(shuō)明這一點(diǎn)。Caldwell測(cè)試沒(méi)有為被告提供排除條件,如果他不符合一個(gè)合理的人的特征,即:一個(gè)人由于智力不足等原因,預(yù)見(jiàn)風(fēng)險(xiǎn)的能力確實(shí)減弱,如Elliot訴C案。另一個(gè)原因是,如果像W訴Dolbey案中那樣,對(duì)與魯莽有關(guān)的不同罪行進(jìn)行不同的測(cè)試,可能會(huì)產(chǎn)生混亂。被告人根據(jù)《惡意損害法》按照Caldwell的客觀檢驗(yàn)標(biāo)準(zhǔn),對(duì)魯莽地造成眼鏡的損害負(fù)有責(zé)任,但根據(jù)《1861年侵犯人身罪法》按照Cunningham的主觀檢驗(yàn)標(biāo)準(zhǔn),對(duì)毀壞眼睛的行為不負(fù)有責(zé)任。這種對(duì)魯莽行為測(cè)試的沖突是沒(méi)有意義的,因?yàn)榉伤坪鯇?duì)眼鏡的保護(hù)多于對(duì)眼睛的保護(hù)。
盡管一些學(xué)者傾向于客觀測(cè)試,但R訴G案仍然是主要的權(quán)威。自R訴G案以來(lái),《法典草案》經(jīng)過(guò)改革,并在《刑法法案》下進(jìn)行了轉(zhuǎn)載,進(jìn)一步簡(jiǎn)化了法律。總之,在法律上,個(gè)人應(yīng)該為其行為負(fù)責(zé)。盡管花了一個(gè)多世紀(jì)的時(shí)間,我們現(xiàn)在有了正確的平衡,目前的主觀測(cè)試是一個(gè)公平的測(cè)試,被告將根據(jù)個(gè)人情況或特征以及他在冒險(xiǎn)時(shí)的主觀心態(tài)來(lái)判斷。 深圳燕羅路刑事律師事務(w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