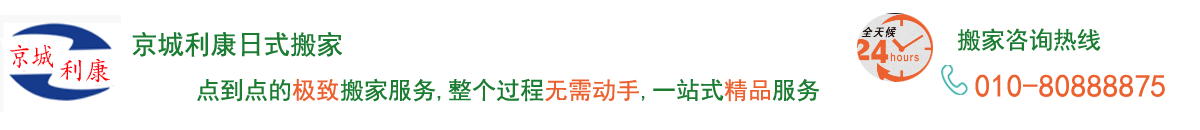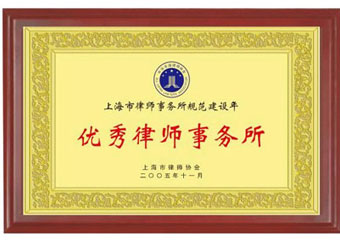在印度,在大多數(shù)涉及富人和有影響力的人或腐敗的政客的案件中,證人變成了敵對(duì)者,使法治成為一種嘲弄。很多時(shí)候,證人變得無法追蹤。有時(shí),他們就這樣被消滅了。長(zhǎng)期以來,刑事司法系統(tǒng)一直面臨著這個(gè)嚴(yán)重的問題,但沒有任何可行的、全面的解決方案。在繼續(xù)本文的研究之前,研究人員建議先看看下面的例子,這些例子突出了情況的嚴(yán)重性。
-在BestBakery案的審判中,有21人被列為被告,檢方主要依靠幸存者ZahiraSheikh的證詞。然而,在新組成的法庭上,她拒絕指認(rèn)任何被告,這與她在警方和國(guó)家人權(quán)委員會(huì)面前的陳述不一致。后來她斷言,由于受到威脅和對(duì)生命的恐懼,她說了謊。在這種情況下,目前的法律制度是否有任何補(bǔ)救措施?
-杰西卡-拉爾(JessicaLal)案中,她被一位部長(zhǎng)的兒子槍殺,最終也被打敗了,因?yàn)殡S著審判的進(jìn)行,大多數(shù)證人都變成了敵對(duì)者,收回了他們的陳述。
-在1999年的寶馬肇事逃逸案中,前海軍參謀長(zhǎng)和海軍上將SLNanda的孫子SanjeevNanda醉酒后據(jù)稱在德里碾壓了正在睡覺的人行道上的居民。除了變得敵對(duì)的證人外,事故中唯一的幸存者也告訴法庭他是被一輛卡車撞倒的,而關(guān)鍵證人則拒絕確認(rèn)那輛寶馬車。
- 這些被炒作的事件將敵意證人的問題推向了中心舞臺(tái),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事例只是整個(gè)刑事司法系統(tǒng)被這一問題破壞的大背景的一個(gè)預(yù)告片。重要的是,我們要找出當(dāng)前刑事司法系統(tǒng)中的漏洞,這些漏洞允許不擇手段的證人和有錢有勢(shì)的人顛覆正義的理想。
- 對(duì)于消除敵意證人的弊端,特別是在高調(diào)的案件、涉及名人的聳人聽聞的謀殺案和針對(duì)少數(shù)民族的犯罪中,可能有哪些解決方案?需要對(duì)現(xiàn)行立法進(jìn)行哪些修改,以提供有效的檢查和勸阻證人轉(zhuǎn)向敵意?證人保護(hù)計(jì)劃是否提供了任何可行的解決方案?為了尋求上述問題的答案,研究者試圖提交這篇關(guān)于"敵意證人"的論文。
- 在刑事司法系統(tǒng)的迷宮中,舉證責(zé)任主要由控方承擔(dān),案件的全部?jī)r(jià)值取決于證人。根據(jù)其定義,證人是指在某個(gè)事件中在場(chǎng)并能提供相關(guān)信息的人。換句話說,證人是一個(gè)人,為了能夠在審判期間證明某一事件或事故,他的存在是必要的。正如Bentham所說,"證人是正義的眼睛和耳朵"。
然而,在1973年的《刑事訴訟法》中,這個(gè)詞并沒有明確的定義。同樣,《印度證據(jù)法》也沒有明確提到"敵意證人"這一短語(yǔ),這一術(shù)語(yǔ)是從普通法中采用的。在普通話中,敵意證人被理解為與詢問證人的一方立場(chǎng)相悖的人,即使律師傳喚證人代表其客戶作證。當(dāng)證人變得公開對(duì)立并作出不一致的陳述時(shí),律師可以向法院請(qǐng)求宣布他為敵意證人,從而獲得盤問他的機(jī)會(hu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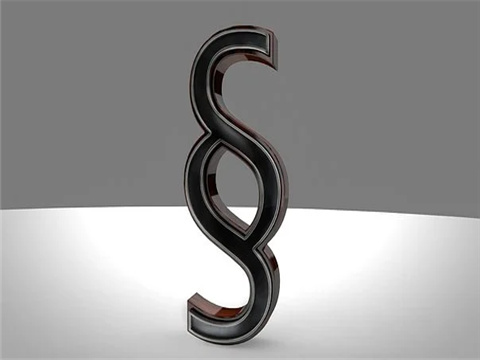
有敵意的證人
2.1第162條--概述。
從立法的歷史和已判決的案例來看,該主要條款的目的是全面禁止使用在警察面前作出的陳述,而頒布條款明確規(guī)定,向警察作出的陳述不得用于任何目的。但書中規(guī)定了一般禁止的例外情況,即陳述可以按照《證據(jù)法》第145條規(guī)定的方式用于反駁證人。
2.2本節(jié)的目的。
(a)本條保護(hù)人們不被警察記錄的陳述所束縛,因?yàn)樗私咕飓@取陳述者簽名的規(guī)定。
(b)本條及第161條實(shí)際上載有法律保障措施,以保護(hù)被告人免受警方過度熱衷的行動(dòng)所影響,因?yàn)樵谧鞒鲫愂鰰r(shí)已知有一項(xiàng)調(diào)查正在進(jìn)行之中,警方可能會(huì)對(duì)作出陳述的人施加影響,也免受那些明知調(diào)查已經(jīng)開始而準(zhǔn)備說不實(shí)之言的人所偏見。
(c)該條規(guī)定了一個(gè)普遍禁止使用證人在調(diào)查期間在警察面前作出的陳述的規(guī)定,其假設(shè)是上述陳述不是在令人信任的情況下作出的。這一立法假設(shè)加上警察調(diào)查敷衍了事的正面證據(jù),將使警察記錄的任何陳述失去信譽(yù)。
(d)法律容許警務(wù)人員取得這些陳述,以便于調(diào)查罪行和鼓勵(lì)自由透露資料。然而,法律卻規(guī)定這些陳述不得接納為證據(jù),原因很明顯,就是這些陳述會(huì)被人懷疑是否屬于自愿性質(zhì),即這些陳述可能并非屬于自由和公正的。
非常清楚的是,由于對(duì)警察的不信任,立法機(jī)構(gòu)確保了證人向警察所做的陳述在法庭上沒有證據(jù)價(jià)值。然而,與此同時(shí),作為事件發(fā)生后不久證人陳述的最早記錄,其中發(fā)現(xiàn)的任何矛盾都會(huì)對(duì)否定證人的證詞有巨大的幫助,因此,該條的構(gòu)想是試圖通過媒體找到一種幸福。該條第(1)款的但書所規(guī)定的程序的全部基礎(chǔ)是這樣一個(gè)原則:作出不一致陳述的證人是不可靠的。
2.3第1分節(jié)的但書。
該但書允許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有限度地使用以前的陳述,這些情況如下。
-該證人必須是為控方傳喚的。
-使用者是被告人,或經(jīng)法庭批準(zhǔn)后是控方。
-根據(jù)《證據(jù)法》第145條,該陳述是為了反駁該證人而使用。
-有關(guān)證人的陳述必須是書面形式的;以及
-該書面陳述必須得到證明。
這些條件中的一些已被簡(jiǎn)要討論如下。
(a)證人必須是為起訴而被傳喚的。
如果證人被辯方傳喚,根據(jù)《證據(jù)法》的規(guī)定,控方或辯方都不能利用他以前的陳述來反駁或證實(shí)他。這一點(diǎn)甚至適用于由法庭傳喚的證人。
(只有被告并經(jīng)法院許可,控方才能使用該陳述。
根據(jù)本條規(guī)定,控方可以為本條所準(zhǔn)許的有限目的使用陳述,但必須得到法庭的準(zhǔn)許。除了本節(jié)規(guī)定的程序外,《證據(jù)法》第154節(jié)還允許法院允許控方對(duì)其可能傳喚的證人進(jìn)行交叉詢問。相反,被告/辯護(hù)方有權(quán)根據(jù)本節(jié)規(guī)定使用陳述,而無需得到法院的任何許可。
(c)不可能進(jìn)行確證。
警方在調(diào)查期間記錄的證人陳述不能用于為控方故事尋求保證。本條規(guī)定的陳述嚴(yán)格來說只能用于《證據(jù)法》第145條規(guī)定的反駁證人的目的,"不能"用于任何其他目的。它不能被用作有利于或不利于被告的實(shí)質(zhì)性證據(jù)。但是,控方可以利用它來證明證人對(duì)警察所陳述的內(nèi)容的抗壓程度。
(d)陳述必須得到適當(dāng)?shù)淖C明。
陳述中用于反駁證人的部分必須得到證明并記錄在案。陳述的任何部分,如果獲得適當(dāng)證明的話",這句話犟調(diào)了證明證人陳述的必要性,即必須證明所記錄的陳述中用作反駁的部分,確實(shí)是證人向調(diào)查人員所說的話。
要做到這一點(diǎn),可以在警察進(jìn)入證人席時(shí)特別詢問證人是否向他作了這樣的陳述,以及他是否作了記錄。這聽起來有點(diǎn)不切實(shí)際,因?yàn)榇蠖鄶?shù)案件都是在記錄了這些陳述之后才進(jìn)行審判的,而且鑒于頻繁的轉(zhuǎn)移,調(diào)查人員對(duì)陳述的真實(shí)性進(jìn)行宣誓是不切實(shí)際的。然而,由于缺乏任何其他有效的機(jī)制,人們不得不依靠這種機(jī)制。
還有人認(rèn)為,展示的整個(gè)陳述或展示的整個(gè)案件日記并不能證明陳述。當(dāng)然,可以通過讓證人承認(rèn)他確實(shí)做了陳述來證明該陳述,但鑒于上述決定,適當(dāng)證明陳述的任務(wù)變得更加困難。
上述論點(diǎn)在以下程度上是荒謬的:援引如此多的不信任,以至于《刑事訴訟法》中的有關(guān)條款被頒布的同一名警察,將被依賴來適當(dāng)?shù)刈C明陳述。其次,如果這種證據(jù)是可以接受的,令人驚訝的是為什么展示案件日記和整個(gè)陳述是不夠的。相反,鑒于警察局沒有攝像頭,周圍也沒有太多的人,他們可能會(huì)聽到陳述,并在以后證明它確實(shí)是由警察提供的,因此,"不"接受警察的證據(jù)也是荒謬的。
在某一案件中,有人錯(cuò)誤地指出,在盤問證人之前,沒有必要對(duì)記錄進(jìn)行證明,以引起證人的注意。據(jù)認(rèn)為,該條中使用的"必須"一詞清楚地表明,在證明陳述之前有義務(wù)提請(qǐng)證人注意。法院的上述意見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法院可以自由裁量這兩者中的哪一個(gè)應(yīng)該先于另一個(gè),并且在這個(gè)程度上是有缺陷的。
2.4《刑事訴訟法》第162條對(duì)《證據(jù)法》第145條。
與《證據(jù)法》第145條不同的是,該條的但書直接賦予了通過證明第161(3)條記錄的陳述來確定矛盾的權(quán)利。第145條分為兩部分,都涉及到交叉詢問。第一部分涉及除矛盾方式外的交叉詢問,第二部分只涉及矛盾方式。鑒于第162條第1款的規(guī)定,《證據(jù)法》第145條的第一部分不能適用于對(duì)該條規(guī)定的陳述進(jìn)行交叉詢問。
控方證人'不能'只被問及他以前是否曾向調(diào)查的警務(wù)人員作出相反的陳述,而事情則告一段落。平心而論,必須尖銳地提請(qǐng)他注意陳述中相互矛盾的相關(guān)段落,而僅僅詢問他先前是否普遍作出過另一份陳述是不夠的。然而,在這樣做的同時(shí),向證人宣讀整個(gè)陳述被認(rèn)為是不恰當(dāng)?shù)某绦颉WC人的回答也不能作為證據(jù)使用,而只能用于通過這種書面形式來反駁證人的目的。此外,應(yīng)給予證人合理的機(jī)會(huì)來解釋矛盾之處。
第145條授權(quán)法院酌情允許傳喚證人的人向他提出任何可能被對(duì)方盤問的問題。這意味著在提出同樣的請(qǐng)求時(shí),可以宣布他為敵方。但是,只有在表現(xiàn)出敵意的情況下才能給予許可。僅僅提供不利的證詞或在這里或那里犯了一個(gè)錯(cuò)誤,都不是讓證人被宣布為敵意的適當(dāng)理由。
2.5當(dāng)遺漏相當(dāng)于矛盾時(shí)。
該解釋明確規(guī)定,只有當(dāng)法庭認(rèn)為某項(xiàng)遺漏具有重要意義,并與其他方面相關(guān),而且是一個(gè)事實(shí)問題時(shí),該遺漏才構(gòu)成矛盾。因此,法院有責(zé)任通過適用上述測(cè)試來決定這個(gè)問題。
眾所周知,遺漏應(yīng)該是關(guān)于一個(gè)重要的方面,即使沒有問題,證人通常也有義務(wù)或被期望在其他答案中披露該方面的情況,以及在盒子里給出的新版本是否與他已經(jīng)說過的內(nèi)容相抵觸,并作為一種修飾手段。輕微的遺漏并不等同于矛盾。相反,只有那些通過必要的暗示導(dǎo)致在警察和法庭上的陳述之間出現(xiàn)沖突的遺漏才會(huì)構(gòu)成矛盾。
然而,值得贊賞的是,法院一直有意識(shí)地不把構(gòu)成矛盾的遺漏范圍擴(kuò)大到太遠(yuǎn)。首先,警方根據(jù)第161條記錄的陳述通常是陳述的實(shí)質(zhì)內(nèi)容,小的細(xì)節(jié)總是被遺漏。這種遺漏并沒有被算作是矛盾。記憶錯(cuò)誤,特別是當(dāng)證人被傳喚到法庭前作證時(shí),在陳述實(shí)際作出后很久,是造成遺漏的另一個(gè)重要原因,法院為這一點(diǎn)留有足夠的余地,也適當(dāng)?shù)爻姓J(rèn)了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即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記錄的陳述不是證人所說內(nèi)容的逐字再現(xiàn)。
法院認(rèn)為,除非在法庭上的陳述與警方的陳述不可調(diào)和,否則警方陳述中的遺漏不能被視為是矛盾的。
2.6宣布證人為敵意。
在本章的最后,研究者試圖對(duì)如何宣布證人為敵意以及為此需要遵循的步驟的順序進(jìn)行簡(jiǎn)要總結(jié)。
(a)首先,可以在不向證人出示書面材料的情況下對(duì)其進(jìn)行盤問。證人需要在法庭上重述他在調(diào)查期間所說的內(nèi)容。但是,他可以不這樣做,也可以否認(rèn)曾經(jīng)做過這樣的陳述。如果很明顯證人變成了敵意,控方可以請(qǐng)求說證人變成了敵意,并獲得對(duì)他進(jìn)行交叉詢問的許可。直到這個(gè)階段,"適當(dāng)證明"該陳述是不需要的,因?yàn)檎降姆瘩g程序還沒有開始。
(b)然后必須提請(qǐng)證人注意陳述中用于反駁他的那些部分。
(c)那么該陳述必須"得到適當(dāng)?shù)淖C明",即一般來說,該特定案件的調(diào)查人員需要證明該陳述是實(shí)際作出的。
(d)如果該陳述得到適當(dāng)證明,被告或檢方在得到法庭允許的情況下可以用它來反駁證人,從而對(duì)他的可信度提出質(zhì)疑。
第一步和最后一步之間有一個(gè)非常重要但又微妙的區(qū)別。第一步只是使控方能夠參照證人以前的陳述對(duì)其進(jìn)行盤問,而不是彈劾其可信度。這將有助于通過這種交叉詢問引出對(duì)當(dāng)事人有利的材料,甚至不需要訴諸于第二部分規(guī)定的程序。第145條并沒有以任何方式限制在不向證人出示其先前書面陳述的情況下進(jìn)行盤問的權(quán)利。它所規(guī)定的是,如果打算對(duì)他進(jìn)行反駁,則應(yīng)提請(qǐng)他注意該書面材料。盤問和反駁之間的區(qū)別必須始終牢記在心,以便能夠理清粗略閱讀第162和145條時(shí)可能出現(xiàn)的任何模煳之處。
2.7宣布證人為敵意的影響。
由于沒有任何法律規(guī)則規(guī)定先前的陳述應(yīng)被視為正確,而隨后的陳述應(yīng)被視為虛假,因此證人所做的陳述應(yīng)被拋棄,從中得到的唯一作用是測(cè)試證人的可信度。
如果法院發(fā)現(xiàn)證人被他以前的陳述所反駁,它可以全部或部分地拒絕他的證據(jù),但這不能成為假設(shè)證人在法庭上說了假話的理由,法院不能僅僅以這個(gè)理由根據(jù)第344條啟動(dòng)提供虛假證據(jù)的程序,因?yàn)槌说?61條規(guī)定的陳述外沒有其他材料。
在研究了宣布證人有敵意的程序后,有必要研究一下法律中的漏洞,這些漏洞很難阻止證人變得有敵意。
3.缺陷、分析、修正和解決方案
3.1"缺陷"--對(duì)法律的批評(píng)。
(a)第162條。目前的這一條款只能用于反駁證人之前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161條記錄的陳述,為此,它明確規(guī)定了一項(xiàng)禁令。
-該條限制性太強(qiáng),只允許對(duì)控方證人進(jìn)行盤問,從而使辯方證人根據(jù)第161條所做的陳述絕對(duì)是多余的。這也意味著不能對(duì)辯方和法庭證人所作陳述的真實(shí)性提出質(zhì)疑,這是一個(gè)明顯的缺陷,需要加以彌補(bǔ)。在某些案件中,法院還指出,不幸的是,印度法律不允許對(duì)辯方證人以前在警察面前的陳述進(jìn)行交叉詢問。
-其次,該條款的另一個(gè)嚴(yán)重缺陷在于它不允許對(duì)證人的證詞進(jìn)行確證,在這一點(diǎn)上與《證據(jù)法》第157條的規(guī)定相悖。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司法工作。對(duì)警察的不信任雖然在一個(gè)多世紀(jì)前就有了,但仍然像以前一樣強(qiáng)烈,超出了實(shí)際需要的范圍。
-第三,該條規(guī)定嚴(yán)格禁止讓被告簽署聲明,以保護(hù)他們不受警察的脅迫和脅迫,這也是源于對(duì)警察的不信任。必須指出的是,這種懷疑所帶來的代價(jià)是很高的,因?yàn)樗膭?lì)證人在審判期間出爾反爾,做出不一致的陳述。在陳述上簽字可能有助于勸阻證人轉(zhuǎn)為敵意并阻止偽證罪的發(fā)生。
總的來說,本節(jié)是以被告為中心的程序法的完美體現(xiàn)。它保證了被告的絕對(duì)和不可侵犯的權(quán)利。相反,警察承擔(dān)了非常沉重的責(zé)任,即使對(duì)證人的陳述有一點(diǎn)懷疑,也會(huì)削弱他們的價(jià)值和他們本來具有的一點(diǎn)效用。
(b)法律中鼓勵(lì)證人采取敵對(duì)態(tài)度的其他缺陷。
(i)目前,在調(diào)查人員面前故意作出虛假陳述并不構(gòu)成犯罪,因?yàn)橄鄳?yīng)的刑法條款,即《印度刑法典》第193條規(guī)定,只有在有義務(wù)說明真相的情況下,才會(huì)對(duì)作出虛假陳述的行為進(jìn)行處罰。與《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一起閱讀,它只規(guī)定在調(diào)查過程中接受警官詢問的人"有義務(wù)回答"與調(diào)查中的案件有關(guān)的所有問題,但回答這些問題有可能使他受到刑事指控或處罰或被沒收的問題除外。由于S.161(2)中的"回答"一詞之后沒有"真正"一詞,IPC第179條中的處罰規(guī)定對(duì)于拒絕回答調(diào)查人員提出的問題的情況并不適用。
這似乎是警察程序法中的一個(gè)嚴(yán)重漏洞,并鼓勵(lì)無良的證人撒謊而不受懲罰。在目前的形式下,該條款未能遏制偽證的惡習(xí),而偽證在我國(guó)相當(dāng)普遍,并阻礙了調(diào)查的進(jìn)行。如果調(diào)查的目的是為了發(fā)現(xiàn)真相,如果公民有責(zé)任通過誠(chéng)實(shí)地提供他所掌握的信息來協(xié)助發(fā)現(xiàn)真相,那么就需要對(duì)該條進(jìn)行修改,使證人有義務(wù)說出真相。
(其次,偽證罪在印度已經(jīng)成為一種被遺忘的罪行,需要更加認(rèn)真地對(duì)待,與其他國(guó)家類似,偽證罪是一種嚴(yán)重的罪行,會(huì)受到嚴(yán)厲的懲罰。對(duì)偽證罪的起訴和懲罰"應(yīng)該是經(jīng)常的和有威懾力的"。要做到這一點(diǎn),就必須迅速、簡(jiǎn)要和非技術(shù)性地審理偽證案件。也許,對(duì)這種審判的公開報(bào)道會(huì)帶來預(yù)期的結(jié)果,即在傾向于為別有用心的被告人辯護(hù)的證人心中產(chǎn)生恐懼。
(iii)法律中沒有專門針對(duì)威脅或恐嚇證人的人的特殊規(guī)定。例如,《伊斯蘭刑法》第503條一般涉及刑事恐嚇,沒有為證人提供任何特別保護(hù)。盡管有人認(rèn)為,即使是恐嚇證人等案件也可以在同一條款下提出,沒有必要制定更多的法律,但有兩個(gè)重要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首先,對(duì)此類犯罪的懲罰應(yīng)該加重,因?yàn)樗鼈兏蓴_了司法,因此更加令人發(fā)指。
-其次,這類罪行是可以保釋的,而且由于調(diào)查和審判的時(shí)間很長(zhǎng),因此證人更有可能得不到救濟(jì),或者救濟(jì)的時(shí)間太晚。
3.2建議的修訂。
(i)印度法律委員會(huì)在其第154次報(bào)告中建議修訂《刑事訴訟法》第164條,以使調(diào)查人員必須獲得所有重要證人的陳述,并由地方法官宣誓后記錄下來。這樣記錄下來的陳述將具有很大的證據(jù)價(jià)值,對(duì)反駁和確證很有幫助,并將阻止證人變得有敵意。因此,有人提議在第164條中增加第1A款。雖然這樣的解決方案是可取的,而且還能保護(hù)證人不受警察的脅迫,但這是非常不切實(shí)際的,因?yàn)檫@需要大規(guī)模地招聘更多的治安法官,只為記錄陳述的目的。
(ii)鑑于修訂建議中的上述限制,第178報(bào)告書提出了另一個(gè)方案,即建議的第164(1A)條應(yīng)限于可判處十年或以上監(jiān)禁的罪行或涉及死刑的罪行。有人大聲疾唿,這樣的建議不需要招聘新的治安法官,目前的數(shù)量就足夠了。然而,不可否認(rèn)的是,鑒于印度的犯罪率,如果擬議的第164(1A)條得到頒布,治安法官除了記錄陳述外,不可能履行任何其他職能。
(iii)《刑事訴訟法》第344條需要修改,以要求法院在認(rèn)為證人在法院審理的案件中有意或故意提供虛假證據(jù)或捏造虛假證據(jù)時(shí),對(duì)其進(jìn)行即決審判(目前,法院對(duì)是否即決審判有酌情權(quán))。
(在現(xiàn)實(shí)中,大多數(shù)法官都忽視了證人出爾反爾的事實(shí),甚至不對(duì)其提出申訴。作偽證幾乎已經(jīng)成為法院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們建議修改《刑事訴訟法》第340條,授權(quán)法院的任何官員對(duì)敵意證人提出申訴。我們還恭敬地提出,法院在處理這些問題時(shí)應(yīng)保持警惕,必須通過培訓(xùn)和要求定期報(bào)告,使下級(jí)法院認(rèn)識(shí)到他們有責(zé)任遏制偽證的威脅。
(v)根據(jù)第164條向裁判官作出的陳述應(yīng)具有實(shí)質(zhì)價(jià)值,即使證人撤回其陳述,亦應(yīng)獲準(zhǔn)用作針對(duì)被告的實(shí)質(zhì)證據(jù),而且應(yīng)以早前的陳述而非審訊期間作出的不一致陳述為依據(jù),因?yàn)榍罢呤窃诰o張的情況下作出,更有可能是真實(shí)的。然而,這種陳述的證明價(jià)值應(yīng)該由法院酌情決定,并根據(jù)盤問和其他相關(guān)事項(xiàng)進(jìn)行評(píng)估。這一論點(diǎn)的反面是,它為警方創(chuàng)造了充分的機(jī)會(huì),使其能夠利用這種情況,使用脅迫性方法從證人那里獲得有利的陳述。
3.3解決方案?
除了擬議的修正案(如果這些修正案得到充分執(zhí)行,將在很大程度上糾正這種情況),一個(gè)可能的解決方案也符合目前的法律和立法情況,即在事件發(fā)生后不久,在裁判官面前記錄證人的陳述,這樣,如果證人在審判期間做出實(shí)質(zhì)性的不同陳述,他們就會(huì)一直擔(dān)心被起訴和懲罰。相反,有一種更激進(jìn)的想法,即向警察作出的陳述應(yīng)被接受。例如,在1987年以前的《反恐怖主義法》中,向警察作出的供詞在某些情況下可被接受為證據(jù),這取決于警察是否具有一定的級(jí)別以及供詞是否自愿作出。在《防止恐怖主義法》中也采用了同樣的框架。與此類似,有人認(rèn)為,向具有一定級(jí)別的警察所做的陳述應(yīng)該被接受。從另一個(gè)角度看,這為警察濫用權(quán)力創(chuàng)造了充分的空間,因?yàn)樗麄兯坪鯖]有做任何主動(dòng)的事情,讓其他人擺脫了不信任。其次,TADA和POTA都是針對(duì)極端情況的,不能轉(zhuǎn)用于所有情況下的所有犯罪。
研究者認(rèn)為,這種解決方案似乎是解決敵意證人問題的最有效和最簡(jiǎn)短的方法。然而,這將引起人們對(duì)刑事司法系統(tǒng)的嚴(yán)重懷疑,并導(dǎo)致許多爭(zhēng)議。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不能從一個(gè)極端的立場(chǎng)轉(zhuǎn)向另一個(gè)極端的立場(chǎng),即從以被告為中心轉(zhuǎn)向以受害者為中心。一旦對(duì)警察部門灌輸了一些信心,這個(gè)解決方案肯定會(huì)成為最可行的方案。為此,警察和立法機(jī)構(gòu)本身必須發(fā)揮關(guān)鍵作用。在目前的情況下,對(duì)警察的不信任實(shí)際上已經(jīng)在《刑事訴訟法》中被制度化。除非這種觀念得到改變,否則我們相信,這種解決方案將導(dǎo)致更多的騷亂,甚至在法庭上的不信任也會(huì)比現(xiàn)在持續(xù)存在。相反,盡管其他解決方案涉及更高的成本和更多的時(shí)間,但它們似乎更有希望,更持久,并為所有人所接受。
最后,我們認(rèn)為,即使所有建議的修正案和解決方案都得到了執(zhí)行,而且證人也不會(huì)僅僅因?yàn)榻疱X利益的誘惑而變成敵對(duì)者,但很難想象,如果由于被告的威脅,證人的生命受到威脅,他將如何反應(yīng)。將他的處境描述為夾在魔鬼和深海之間也不為過,在生命受到威脅的壓力下,他別無選擇,只能在法庭上作偽證。如果這樣的證人因作偽證而受到懲罰,那就違背了自然法的原則。
據(jù)統(tǒng)計(jì)數(shù)字,大多數(shù)無罪釋放都是由于重要證人變得有敵意的結(jié)果。調(diào)查人員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161(3)條記錄的陳述實(shí)際上沒有任何重要價(jià)值,只是被用來指責(zé)證人的可信度。無論如何,社會(huì)風(fēng)氣嚴(yán)重阻礙了任何有正義感的人大膽地說出真相,而給予證人的法律豁免權(quán),無論是出于善意的還是間接的原因,總之鼓勵(lì)了證人的敵意,沒有任何顧慮。只要證人繼續(xù)懷有敵意,不在法庭上作出真實(shí)的證詞,正義就會(huì)受到損害,人們對(duì)司法程序和司法系統(tǒng)的效力和可信度的信心就會(huì)繼續(xù)受到侵蝕和破壞。前總檢察長(zhǎng)索里-J-索拉布吉說。"沒有什么比由于證人轉(zhuǎn)為敵意并撤回其先前的陳述而導(dǎo)致的起訴失敗更能動(dòng)搖公眾對(duì)刑事司法系統(tǒng)的信心。
-雖然在調(diào)查期間向警察提供的陳述可以被接受,這似乎是一個(gè)有效的解決方案,但它確實(shí)帶來了很大的可能性,即它可能會(huì)導(dǎo)致對(duì)刑事司法系統(tǒng)的信仰失敗。由于成本太高,這個(gè)解決方案顯然是不可取的。然而,不可否認(rèn)的是,如果人們的觀念能夠改變,從而對(duì)警察產(chǎn)生更多的信任,這樣的解決方案無疑是理想的。只要這種情況沒有出現(xiàn),我們就會(huì)認(rèn)為這種解決方案會(huì)造成更多的傷害,因?yàn)樗试S濫用的機(jī)制,而不是補(bǔ)救的情況。
-如果認(rèn)為重要證人在調(diào)查期間所做的所有陳述都應(yīng)由治安法官?gòu)?qiáng)制記錄,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gè)"不切實(shí)際"的解決方案。然而,它也有自己的優(yōu)點(diǎn)--(a)它充分考慮到了立法者保護(hù)證人不受警方脅迫的意圖;(b)它在公眾中很受歡迎,不需要改變觀念;(c)它是增加證人所作陳述效用的有效方法,因?yàn)橄虿门泄偎鞯年愂鲆部捎糜谧糇C,而目前的法律立場(chǎng)是向警察所作的陳述只能用于彈劾證人的可信度。
此外,要改變?nèi)藗兊挠^念,遠(yuǎn)比修改一項(xiàng)立法和招聘更多的治安法官要難,因?yàn)榭赡軙?huì)有這樣的需要。 深圳律師事務(wù)所
| 福田福中路律師談火災(zāi)損失的賠償 | 福田福中路律師解答潛在的刑事責(zé) |
| 福中路律師講述警方和CPS之間的關(guān) | 福中路律師講述瑪麗亞案例中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