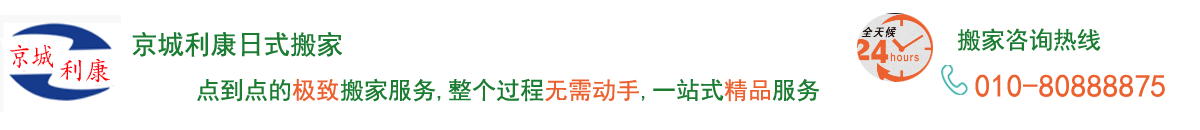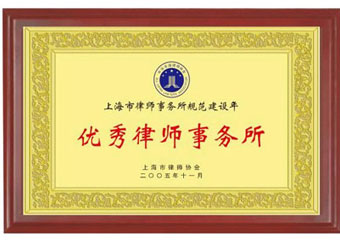在刑法中,嚴格責任是一種犯罪,盡管至少不存在犯罪意圖的一個要素,因此法院在沒有這一關鍵要素的情況下不愿施加此類責任。我會分析什么是嚴格法律責任的罪行,以及法院在考慮是否屬于嚴格法律責任的罪行時解釋法例的方法,我會看看普通法中屬于嚴格法律責任的罪行并列出案例指導法院的法律和原則,并簡要考察其他國家及其制度施加嚴格責任的方式。
在刑法中,嚴格責任是盡管故意、魯莽或可能需要了解犯罪的其他要素。據說責任是嚴格的,因為即使被告真的不知道使他們的行為或不作為犯罪的一個或多個因素,他們也會被定罪。因此,被告可能不會以任何真正的方式受到責備,即甚至沒有刑事疏忽,即犯罪意圖的最不應該受到指責的程度。

嚴格責任出現在 19 世紀,以提高工廠的安全和工作標準。這些法律適用于強制執行社會行為的監管犯罪,其中在定罪后對個人的污名化程度最低,或者社會關注預防傷害,并希望將犯罪的威懾價值最大化。如英國藥學會訴 Storkwain (1986) 2 ALL ER 635 中所見,在個別案件中施加嚴格責任可能非常不公平。 本案的理由是濫用藥物是一種嚴重的社會罪惡,藥劑師應該鼓勵在提供藥物之前采取甚至不合理的謹慎來驗證處方很可能由于在這些罪行中沒有犯罪意圖,普通法不愿意施加嚴格的責任。在普通法中,只有兩項罪行是嚴格責任罪,滋擾罪和刑事誹謗罪。
在 Whitehouse 訴 Lemon Gay News(褻瀆案)或愛爾蘭案 Shaw v. DPP(違反公共道德的案件)中,可以看到普通法嚴格責任犯罪的例子。通常嚴格責任的罪行是法規的產物,法規的解釋和解釋一直是不一致的主題,在英格蘭里德勛爵的評論中,犯罪意圖應被解釋為 Sweet v. Parsley (1969) 中的立法,如下所示:
幾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認為議會無意將那些在所做的事中完全沒有責任的人定為罪犯。這意味著,每當(立法規定)對犯罪意圖保持沉默時,就有一種推定,即為了使議會的意愿生效,我們必須用適當的措辭來要求犯罪意圖。
法定解釋遵循斯卡曼勛爵在 Gammon v. AG for Hong Kong (1984) 中提出的五項原則,愛爾蘭均遵循這些原則:
如上所述,第一個原則是需要有犯罪意圖的推定,如 Sweet v. Parsley 案中所見并在愛爾蘭的 DPP v. Roberts 案中被接受
其次,在處理真正具有犯罪性質而不是監管性質的犯罪時,推定非常強,我們再次注意到里德勛爵在斯威特的評論,他說“議會不打算使犯罪那些在他們所做的事情中絕不應受到指責的人。”
因此,在 Director of Corporate Enforcement v. Gannon (2002) 中,高等法院裁定,對違反 1990 年《公司法》第 187 (6) 條規定的有限處罰表明,該條款所造成的犯罪在性質上并非真正的犯罪,因此推定可以被反駁。
我們可以在 CC v. Ireland a SC 案中進一步看到這一點,上訴人根據 1935 年《刑法修正案》第 1(2) 條被判犯有法定強奸罪并提出上訴。在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中,SC 認為,該條款的這一方面代表了國家違反憲法未能維護受憲法第 40 條保護的上訴人的個人權利,特別是因為憲法第 15 條推定給予那些人是合憲的。本轄區立法機構頒布的法案。
我們可以從這起定罪被撤銷,隨后 1935 年法令第 1(2) 條廢止的案例中看到,當一項罪行真正構成犯罪并受到嚴厲制裁時,對犯罪意圖的要求是非常強的。用法院的話來說,“以嚴重的方式將一個精神上無辜的人定為刑事犯罪,確實嚴重損害了該人的尊嚴和價值感”。
第三,只有在現行法規明確規定或通過必要暗示這樣做的情況下,才能反駁犯罪意圖推定。Walsh J 在 The People v. Murray (1977) 中接受了這一點。在 B v. DPP (2000) 案中,Nicholls 勛爵指出,必要的暗示意味著明確的暗示,可以在法規的文字、犯罪的性質、法規旨在糾正的惡作劇或任何可能有助于確定立法機關意圖的其他情況。
因此,法院必須審查法規的總體目的。如果意圖引入準刑事犯罪,則可以接受嚴格責任以快速處罰以鼓勵未來遵守,例如定額罰款停車違法行為。但是,如果所涉及的政策問題足夠嚴重且懲罰更嚴厲,那么必須檢驗的是,解讀犯罪意圖要求是否會挫敗議會制定特定罪行的意圖,即如果被告可能通過辯解無知而輕易逃避責任,這不會解決議會試圖補救的“惡作劇”。
正如戈達德勛爵 (Lord Goddard) 在布倫德訴伍德 (Brend v. Wood) (1946) 案中所指出的那樣,法院不應輕率地認定犯罪屬于嚴格責任之一:
“對于保護主體的自由至關重要,法院應始終牢記,除非成文法明確或通過必要的暗示排除犯罪意圖作為犯罪的組成部分,否則法院不應認定犯有觸犯刑法的罪行的人,除非他有罪惡感”。
第四,只有當法規涉及涉及公共安全的社會問題時,才可以反駁推定,第五,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為實現立法目標也必須承擔嚴格的責任。在 Lim Chin Aik v. The Queen 一案中,樞密院建議立法所針對的那類人必須通過監督、檢查或勸誡他控制的人或通過改善商業慣例來做某事。
同樣,在 Gannon 案中,高等法院承認嚴格解釋第 187 (6) 條將鼓勵審計師提高警惕,避免參與對他們個人參與的公司的審計。
某些詞,當在法規中使用時表明一般需要犯罪意圖,例如明知、故意魯莽等詞將暗示犯罪意圖要求。有時,諸如引起之類的詞被認為不需要犯罪意圖。在 Maguire v. Shannon Regional Fisheries (1994) 案中,高等法院根據 1959 年漁業(合并)法第 171 (1) b 條的上下文考慮了這些詞的含義,并得出結論認為無論是否構成犯罪故意做的。
同樣,在 Alpha Cell v. Woodward 案中,上議院考慮了 1951 年河流(預防污染)法第 2(1) 條中包含的詞語,威爾伯福斯勛爵得出結論,該部分中包含的詞語“如果他導致或故意允許進入河流任何有毒、有害或污染物質”,導致這個詞的含義很簡單,而故意允許這個詞涉及未能防止污染,然而,這種失敗必須伴隨著知識。然而,威爾伯福斯勛爵進一步表示,“通過注入犯罪意圖及其例外的概念使本案復雜化,是不必要和不可取的。該部分清晰,其應用簡單。
如上所述,可以在至少一種犯罪意圖要素與犯罪行為要素之一不存在的情況下施加嚴格責任,但是,對不帶有社會污名的犯罪施加嚴格責任至關重要。 ,因為在我看來,在沒有犯罪心理的情況下對真正的刑事犯罪施加刑事責任是不公正的。
例如,在美國,只有輕微的違法行為才具有嚴格的責任,例如不需要證明犯罪意圖的停車違規行為。但是,酒后駕駛等違法行為也屬于嚴格責任。我們可以在 Leocal v. Ashcroft (2004) 一案中看到美國最高法院關于驅逐令的案件,該命令被撤銷,因為定罪是一種嚴格責任,并且只有在犯罪是“暴力犯罪”時才允許驅逐”。
自 1978 年以來,加拿大法律也區分了“嚴格”和“絕對”責任的罪行,因此在 R. v. City of Sault Ste-Marie 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針對監管罪行創建了一個兩級的責任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官方將繼續免于證明犯罪的犯罪意圖。然而,嚴格責任的罪行將給予被告盡職調查的辯護——在絕對責任的情況下,這將繼續被拒絕。此外,在沒有明確的相反立法意圖的情況下,法院認為所有監管犯罪都將被推定承擔嚴格責任。
在首席大法官迪克森 (Dickson) 撰寫的判決書中,法院承認了三類罪行:
真正的犯罪:需要某種積極心態(mens rea)作為犯罪要素的犯罪。這些罪行通常通過指控中使用的語言來暗示,例如“故意”、“故意”、“故意”。
嚴格責任:不需要犯罪意圖證明的犯罪。僅此行為就應受到懲罰。被告有責任以合理的方式行事,并為合理的事實錯誤辯護(盡職調查辯護)。法院指出,“如果被告合理地相信一組錯誤的事實,如果這些事實屬實,將使行為或不作為無罪,或者如果他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避免特定事件,則盡職調查辯護將可用。這些罪行可以恰當地稱為嚴格責任罪行。” 這樣做的原因是法院描述了需要定罪標準低于真實犯罪但不像絕對責任犯罪那么嚴厲的一類犯罪。
絕對責任:與嚴格責任類似,這些罪行也不需要犯罪意圖的證明。然而,被告沒有可用的辯護。
如上所述,嚴格責任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具有立法性質的犯罪,法院對立法進行了解釋以評估犯罪是否具有嚴格責任,但是正如上述各點所指出的,嚴格責任犯罪僅應保留用于監管犯罪或簡易程序犯罪的目的以及公眾關注的犯罪,以確保社會的警惕性和保護,而不是帶有嚴厲懲罰或社會污名的犯罪,因為法律認為犯罪包括兩個關鍵要素, actus reus 和 mens rea,以及在沒有犯罪心理的情況下將個人定為罪犯不應是法律的目的。 深圳律師事務所
| 深圳公司法律師視角下的“北京現 | 深圳公司法律師視角:公司的法定 |
| 深圳公司法律師笑談:合伙企業里 | 深圳公司法律師解析:企業如何構 |
| 深圳公司法務律師為您介紹股東抽 | 深圳公司法務律師來講講高管違反 |